那些在媒体中悬而未跳的年轻人,他们的焦虑与信仰营销
最近采访了几个年轻的媒体人。
一水儿的名校背景,在大媒体做新闻,媒体龄最短的一年,最长的六年。他们在最近的一年中都想过跳槽,有的甚至投过简历,面过试,却在签劳动合同的前一夜又改变了主意。

他们想离开媒体的原因是什么?又为什么迟迟下不了决心?在这场纠结和挣扎中,他们真正想要的是什么?带着这些问题,全媒派(qq_qmp)约上几位朋友聊了聊。
“任由这个世界吃掉你,再吐出来”陈小辉 某经济类报纸记者 媒体龄4年
“威廉斯的《斯通纳》怎么说来着:你会任由这个世界吃掉你,再吐出来。”陈小辉带着被熏出来的北京口音半开玩笑式地说。2016年底他推荐记者读这本书,并且提出了一个问题:充满无力感的平庸生活值得经历吗?
陈小辉本科念的是金融学,没去投行,没去证券,没去银行,一心想当个记者。工作四年后,他成为小班里少数没买房的。“我倒也没觉得失落,每个人想要的东西不一样,我那时就是觉得每天追着新闻跑比追着钱跑有意思。”
“2012年刚来实习的时候,带我的老师都非常厉害,我那时候感觉全世界最幸福的事情大概就是采访写稿,有钱没钱都无所谓,反正哥们一人吃饱全家不饿,所以接下来的三年即便身边的人再怎么走,我都没动过这个心思。”让陈小辉第一次想到“跳槽”的节点是2015年,实习时候就带他的老师辞职去了互联网公司。“走之前他问我要不要一起,可那时我的合同还没到期,而且也觉得自己和他还差得比较远,不知道跟着他过去能做什么,而且我对新闻还是有热情,毕业时候放着证券公司都不去,为了挣钱的话又何必去企业呢。”

2016年,陈小辉结婚了,同一年报社改变了薪酬制度,调低了底薪,稿费占的比重更多,陈小辉的工作比以往更忙了。“从经济上来讲,我理解这种做法,但并不认为这是对的,现在大家都会多做一些快稿,多出些差。你知道,我很久没写过长线大选题了,最怕的是武功全废了。有时出差半夜回来,会忽然有种不安全感,不知道自己在忙什么。”2017年春天,陈小辉投了一些简历,有网络媒体,有涨势不错的内容创业公司,还有咨询公司,最后他拿到了其中两家的offer。
“纠结了有一个月吧,我是学经济出身,笔记本上分析了各种风险和成本,可依然做不出一个果断的决定。后来我就想如果从现有的条件推导不出一个结果,那么不然就做个十年的假设,假设我继续留在这里呆十年,那么会发生什么?然后我就想起《斯通纳》里面的一段描写:‘他已经四十二岁,往前看不到任何自己渴望享受的东西,往后看不到任何值得费心记住的东西’,忽然就打了个冷战。于是迅速做了决定,走。”

陈小辉说其实他自己也并不清楚热情是在哪一个时刻消耗殆尽的,“这世界上有的是和我一样盘缠不够却又志在千里的难兄难弟,有无数不合理却又运转有效的规则。你本以为是事业的东西,最终还是被消耗成了一个职业,而选择一个职业的标准是理性成分更多的。”采访结束,陈小辉有些怅然若失,他反复捏着咖啡杯手柄,仿佛下一秒就能再塑一个形状似的。他说是想起了一段小说中的话:你还躺在这里纳闷,到底做错了什么?因为你总是对这个世界有所期待,而它没有那个东西,也不希望如此。
“这种焦虑不是我个人的”夏南 《中国日报》记者 媒体龄6年
“我的case比较特殊,因为原来不是学新闻的,应该说是误打误撞进了媒体这行。当然还是比较看重媒体的属性,会觉得体制内的传统媒体平台比较大,也比较权威。而且六年前新媒体也没有很兴盛,六年工作里关于新闻的采写,对问题分析的角度,我所在的新闻机构还是给了充分的锻炼,特别是传统媒体分口会比较细,利于记者在一个领域内精耕细作。”夏南说起他的入行之路。
近一年中,他有想过换工作,甚至投过简历。两相不巧,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拍即合的。说到底,夏南珍惜的是职业习惯中某种严肃的东西,在他看来,这种东西以什么形式表现出来并不那么重要。

“很多人按照传统媒体、新媒体区分媒体,将它们对立,这一点其实我并不完全同意。因为说到底新闻还是做内容,没有好的内容,形式都是哗众取宠,无论媒体走到哪个阶段,涉及的内容还是分为政治经济文化等几个方面。与其说我选择没有离开传统媒体不如说我没有选择离开文化报道。而恰恰目前相对比较沉稳的传统媒体的报道风格我更喜欢,很多时候文化报道的噱头太多,认真做采访的故事却越来越少,所以还是希望能把现在跑的领域进一步了解,就算转行也更有底气和积累。”

夏南不相信有时候形式就是会大于内容的,或者说有时候形式至少会等于内容。“要说国外这样的长年积累并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,永远保持好奇心和专业精神是媒体人最好的素质,但是在中国的新闻业传统媒体却被贴上了很多固化的标签。”
“这种焦虑与其说是我个人的,不如说是整个新闻业的焦虑:直播、短视频固然给新闻传播新的平台,也有更大的流量,但坦白说有些时候直播的内容并没有意义。为了直播、航拍、VR 就把这些技术一股脑儿用上,反而稀释了真正有价值的信息。这种情况在传统媒体运用新媒体时候尤其明显,为了追上潮流,传统媒体的一些新媒体作品会形式大于内容,却忘了真正的新闻点和自己擅长的 采写。”
“太早”or“太晚”王三水 某省级党报记者 媒体龄1年
用王三水的话来说,“新闻学一个专业我就读了7年,说弃就弃哪那么容易。”本科四年,研究生三年,王三水念的是国内知名的新闻系之一。在2016年媒体记者岗普遍缩招的大势下,经过层层筛选,进入到现在这家坐落在市中心的报业大厦。
“其实想法特别单纯,就想当个记者,跑跑突发、或者跑跑条线就很开心了。”可大概是进报社花光了运气,王三水被分到副刊,几乎没有出去采访的机会。“每天在做资料的汇编和整理,虽然比较轻松,但内心总有种想跑出去采访的冲动,尤其是上班总路过从前的《申报》馆改建成的咖啡馆,那感觉特别胃疼。”

“我找领导聊了几次,但确实一个萝卜一个坑,很难匀出一个岗位。那时候我忽然想到了跳槽。”王三水这一年间面过几家媒体,拿到了其中一家的offer,可他却放弃了。“其实我有种进退两难的感觉,如果我不是一个27岁的新人,我大概会果断折腾。做决定的那个晚上,我看了看这大半年出的版,其实还是挺有成就感的。真走了的话,这一年的积累可能也会白费,我大概是缺少‘徐图之’的耐心。”
“另外一方面,除了不能时时出去采新闻之外,现在这个工作倒也挺好的,有前辈帮助成长,气氛也比较单纯和谐。”王三水最终决定留在现在这家报纸,用他的话来说是“练内功”,因为还没想清楚一个问题:现在这个年纪、这个境况再做一次选择,是太早还是太晚。
“沉没成本”与“更好的可能性”晓烁 新华网编辑 媒体龄3年
“想做媒体因为想要观察这个世界。认识不同的人,去不同的地方。而且本来也是念的这个专业还是不想荒废掉。”晓烁新闻系本科毕业后去了新华社《参考消息》下属的一个子刊物,“我那时候是一心想要去新华社,但竞争非常激烈,所以就走了‘曲线救国’的路,先进去再说。”

晓烁被分派做房产版块,用她的话来说,就是“明目张胆做软文”。“版很小,事情很少,一起工作的年纪都比较大,忍受的成分比较多,但还是尽最大努力把事情做好,尽力去积累资源,因为我知道不会在这里太久,我的个人习惯也不允许我浪费时间。”一年后,她被调到新华网,比预计的快。
“同事都变成了年轻人,气氛很好,我很喜欢这个团队,只是这次又转去做医疗健康了,房产的资源用不上。”团队的问题解决了,新的问题又来了。“对一个表达欲旺盛的年轻人来说,不能做原创是件痛苦的事情,许多选题是任务性的。”在这个岗位上待了一年后,晓烁动了离职的念头,投过一些简历,面过一些岗位,可始终也没下得了决心。

“我只是觉得那些工作也没有让我看到更好的可能性。现在工作上的事情轻车熟路,也积累了一些资源,换个地方的话比较担心沉没成本。另外就是即便是换工作,还是希望做媒体,这样看来似乎也没有哪个选项是有绝对优势的。”晓烁有许多有趣的朋友,许多是因为工作认识的,她说自己喜欢媒体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能认识很多有趣的人,在她看来,这些人际关系也构成了一部分的沉没成本。
和记者聊了两个小时后,晓烁谈起她的焦虑:“比如直播、短视频、知识付费等等,其实我的认识比较外围,例如领导说这个数据需要可视化一样,那么我们会去找专业的设计同事做成静态或动态图表,但我并不认为真正自己掌握了这门技能就能消除焦虑,因为我不认为自己学了就能有专业的同事做得好,术业有专攻吧。”
“所以,所谓的技能焦虑不在我会不会用一个东西,会不会拍一个东西。而在于因为没有深入参与,而造成的认知空白和心态傲慢。这些概念本身没什么难理解的,但可怕的是对一个新生事物的理解仅仅停留在概念上。它的玩法有哪些不同?它新定义了哪些规则?为什么说它是潮水的方向?回答不上这些问题,才是我的技能焦虑。”

“还会常常冒出想要跳槽的想法吗?”“会呀,比如昨天,同事在饶有兴趣地谈论街上出现越来越多的小黄车,大惊小怪地分享使用心得。我当时在想都炒了多久的话题了,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,怎么可以如此后知后觉。”晓烁半开玩笑式地说。
那些引而不发的,如潮汐般的小冲动,总是时不时把你往前送一送,要你做一个决定,而其实所有纠结做选择的人心里早就有了答案,他只是缺少点坚持或改变的勇气。所以路遥在《人生》感叹:人生,其实无非是矛盾与选择的综合体,无关对错,仅仅在于我们能否有勇气在矛盾中作出选择并勇敢承担一切的后果。
用《星球大战》里Yoda大师的话来说就是: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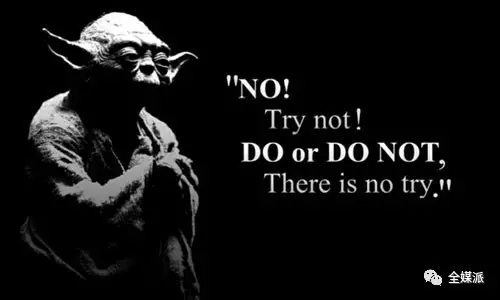
来源:全媒派
1. 遵循行业规范,任何转载的稿件都会明确标注作者和来源;2. 的原创文章,请转载时务必注明文章作者和"来源: ",不尊重原创的行为 或将追究责任;3.作者投稿可能会经 编辑修改或补充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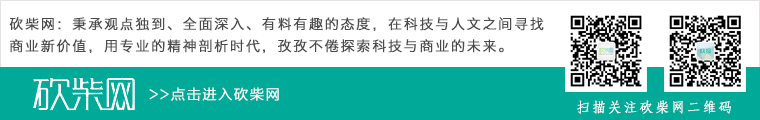



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2797号
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2797号